触摸“商代水门”最真实模样 “小古城遗址”考古有新惊喜
离良渚不远处的三千年前越地中心到底藏着怎样的文明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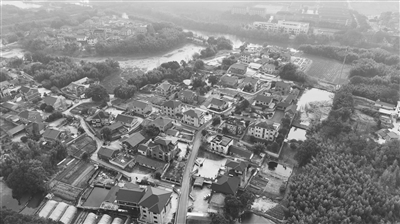

小古城遗址庙山发掘区的人工堆筑台体。
从市中心出发,沿着G235国道一路前行,穿过一片片田野和村落,驱车四十余公里后,我们来到藏在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内的“3000年前越地中心”。
“小古城遗址于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考古成果证实,这座晚商时期的浙北古城,建于距今3300年至3000年间,正是当时浙北地区重要的地域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小古城考古项目负责人罗汝鹏博士向我们介绍,“这里离良渚古城遗址直线距离仅约十公里。”
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考古,在去年年底开展的小古城遗址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上官宣了一系列最新考古重要成果——发现并证实了院落型建筑群、水门、人工堆筑台体等商时期重要遗迹。
良渚文明以后,中国东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子?
人们所熟悉的越国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那场研讨会上官宣的这些发现,如同一块块“记忆碎片”,拼凑起良渚文化衰落后直至吴越争霸兴起之前的这段两千余年的历史空白。
循着遗址,我们走进3000年前的小古城,试图揭开千年历史的神秘面纱。
小古城在哪?
在通往北城墙发掘区的小道上,两边栽着树木和竹子,大棚里还有村民种下的蔬果。“在三千余年前,我们脚下的小道极有可能是当时村落的护城河,而一旁高出地面半米多的不起眼的土埂,经证实,这便是北城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松阳博士告诉记者。
在小古城遗址,我们一遍遍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
城内人们以农耕、养殖为生,依靠水陆交通通行,城外水网密集,水网周边沼泽密布,一幅三千年前的江南水乡图,在我们面前徐徐铺开。
这座三千余年前的浙北古城,城墙在地面以上仍多有保存,城内面积约25万平方米,2015年启动的小古城遗址第一期考古,对南、北两条城墙进行了考古发掘,准确确定了城址的年代和建筑方式。
而在小古城外围存在多个小规模的遗址点,可能是城址外的生产区,也可能是平民的集聚区,与城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小古城遗址就有先民居住,其后崧泽、良渚、广富林文化的人群持续居住繁衍。而最主要的文化堆积形成于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末期至商代。”罗汝鹏介绍,“从小古城遗址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已过去四十余年,但在最近的考古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重要商代遗迹,让我们非常惊喜。”
这次考古发掘主要是在庙山发掘区、北城墙发掘区、湖西发掘区三个范围展开。而近期官宣的一系列重要遗迹也与之相对应,分别为庙山发掘区-庙山高台建筑、北城墙发掘区-水门遗迹、湖西发掘区-商代院落型建筑群。
每一项考古成果的提出,都为我们打开一扇古老世界的大门。跟随着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脚步,我们接连走进这三个挖掘区,再次见证了我国深厚而悠久的文明底蕴,同时也对古人对于建筑方面的智慧以及强大的毅力感到惊叹。

小古城遗址北城墙水门遗迹,保存较好,是国内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同类型遗存。
小古城发现了什么?
“这是迄今为止在同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最大的一座高台!”爬上小古城内地势最高的庙山山顶,李松阳抬起手,指向一座气势恢宏的人工堆筑台体。
眼前的台体占地超1800平方米、相对高度为8米至12米,完全由人工建筑。对于该台体的考古发掘,研究所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弄清楚它是怎么堆筑起来的;二是了解它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我们根据土的颜色的细微差别进行画线,在一步步剖析后,确定了庙山是人为建造的,也大致明白了它的建造方式。”李松阳介绍,“山脚部分,是像梯田一样错落地叠上去,也有点像金字塔的建造方式,堆一层,收一些,然后一层层往上缩。堆了3-4米的高度之后,堆筑的方向从南北调整至东西继续交错着往上夯,最终形成一座土山。两个方向形成垂直交错的直角,两股力量顶住,很扎实不会往两边倒。”
三千多年前,在人力和施工条件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耗费如此大的力气去堆这样一座高台,其中必然有重要意义和特殊价值。
“曾有一种推测说,这会不会是一座大型墓室。经勘测,这一猜想已被否认。”李松阳说,“我们根据高台上的柱洞,推测出高台顶部有一座‘凸’字形的建筑,面积不到一百平米,朝向正南北,在这个‘凸’字形大建筑北侧还有两个小建筑,这种形态更符合宗教祭祀的建筑。此外,我们也认为,古人还会来这里瞭望、观星等。”
而在高台底部也发现了两组建筑,研究所推测可能是给祭祀的人用来休息的,“一般的祭祀建筑都会有这样的配套。”李松阳说。
来到北城墙发掘区的时候,工人们正在加固水门四周的土墙,水道间埋着的木头,正是三千余年前的遗迹,被黑布包了起来,“研讨会上几位水利专家提出,要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去加强对木构遗存的保护,这对未来也是重要的财富。”李松阳说。
北城墙发掘区的水门遗迹是一处南北走向完整的木制结构设施,宽2-3米,内含丰富的木构件遗物。结构非常清晰,对木头的加工痕迹也保留得很好。
水门,即古代水闸。建在河床或河湖岸边,用以控制水位、取水或泄水的建筑物。自古代出现治水活动开始,可能就有了水门。记者了解到,那时候的小古城河网密布,水路系统较为复杂,水门管着水,同样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或许,三千年前的人们就在水门之内取水用水,并进行农业灌溉;又或许,当时的小古城类似“威尼斯水城”,人们以船为交通工具,水门内的河道正是他们的交通系统,具有走船的功能。
“像水门这样的建筑,在中国城市史上当然很常见,但已发掘出的仅有个位数,而有三千年历史并且完全由木构搭建的遗迹更是极为珍贵。”罗汝鹏告诉我们。目前推测小古城有4个城门,都是水门,南边两个、东边和北边各1个,目前已发现两个,发掘的这个是北城墙东侧的水门。
最后,我们走进了昔时小古城人们的“生活区”。
在湖西发掘区,研究所发现了一处商代院落型建筑群,院落里有不同形式的建筑存在,但所有的建筑都是同一个朝向,非常规整,间距也非常明确。
此外,研究所还发现了一处火塘。“这一块泥土颜色偏红,因为经常烧火,把泥土都烧得很红,目前来看是几户人家共用的,猜测是公共聚会的场所。”李松阳介绍。
而在湖西发掘区正北的方位上,有一圈墙体围起的建筑,构造别致。“这里既宽敞又临水,非常适合生活,风水也很好,居住在此的人,身份地位应该比较高。”李松阳说。“经我们判断,城内人的身份已是比较高的,居住在湖西发掘区的这些人家,住的已是很考究,但这还不是城内等级最高的建筑群。通过这些迹象,我们可以窥探到当时社会层级的分布。”
小古城猜想
“太惊喜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像水门、高台这样的建筑在同时代考古中都是不曾发现的,介绍过程中,几位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欣喜溢于言表。
为了进一步了解小古城中的“大乾坤”,记者又和罗汝鹏博士进行了深入交流。
“商代的考古在浙江地区一直比较弱势,小古城遗址的出现或许能拼接起一段约2000年的‘空白’,进一步完善杭州乃至整个江浙地区文明发展的链条。”罗汝鹏笑着说。“目前我们的发现还比较有限,但水门建造以及庙山堆筑的技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考古成果,相信经过未来更为细致的研究和阐释,一个更完整的晚商城池,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华文明的形成经历了“裂变、撞击和熔合”三个阶段,孕育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文明基因,为其绵延不断、持续发展壮大奠定了深厚根基。
小古城遗址的出现便是印证这个观点的代表性展现。“对小古城遗址的探索有利于把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逐渐理顺。良渚时期,‘古国’如‘满天星斗’各自熠熠生辉;之后中原文明渐渐崛起,变得强盛的同时,也将文化渗透到了周边各地,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似乎已是当时人们的共识;直至秦汉一统,中华文明形成统一。”
而小古城时期的文明,有传承、有突破、有交织。“我们的小古城文化,既有对良渚文化的传承,又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碰撞,形成了新的突破。”罗汝鹏告诉记者。
为什么这么说?
宏观地看,小古城时期,虽然大多沿用的仍是良渚的生活生产形式,但在聚落结构、统治模式等方面,已经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
如,小古城遗址像“糖葫芦串”一样的聚落分布模式,在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很常见;在统治形式上,似乎也逐渐与“分封制”或者“采邑制”靠拢。
具象地看,当时小古城人的生活面貌还是以农耕、养殖为主,以舟船为交通工具,这是与良渚乃至河姆渡时期类似的。
但在养殖业、手工业等方面,也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如,小古城遗址包含了丰富的原始瓷器、青铜器等商代遗物,很有可能是从北方以及中原地区流传而来的。“在发掘到的青铜器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浙江独有的特色,比如我们做得更多的是兵器、工具,很少会做礼仪性的容器。再比如,我们采用的是石范铸造,而不是中原常用的陶范。”罗汝鹏介绍。
小古城遗址的考古仍在继续,据罗汝鹏介绍,今年他们将对这次考古的收获进行梳理,然后于明后年继续展开探索。对于小古城遗址的发掘,宛如一扇汇聚古韵今风的珍贵窗口,展现了历史的流转与文化的交融,这也必然能为小古城村的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底蕴,为良渚文化大走廊的建设,再添一颗闪亮明珠。
政协要闻